文/庄雅睿 责任编辑/郑芷萱
看书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苦差事,看过之后,融化那些悲哀才是最难的。
明朝万历年间,徽州商户人家的女儿令秧,在自己十六岁那一年嫁作休宁唐家的填房夫人,唐氏一族是徽州数一数二的富户,丈夫唐简虽比令秧大上几轮但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然而在令秧成为唐家夫人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唐简便因意外离世。二十九年没有出过烈妇的唐氏一族,表面上为着光耀门楣,暗里觊觎朝廷旌表贞节烈妇的好处,像灾民求雨那样期盼令秧成为烈女,他们用尽各种手段诱导令秧殉夫,为了生存,还是天真少女的令秧踏上了艰难而又凶险的烈妇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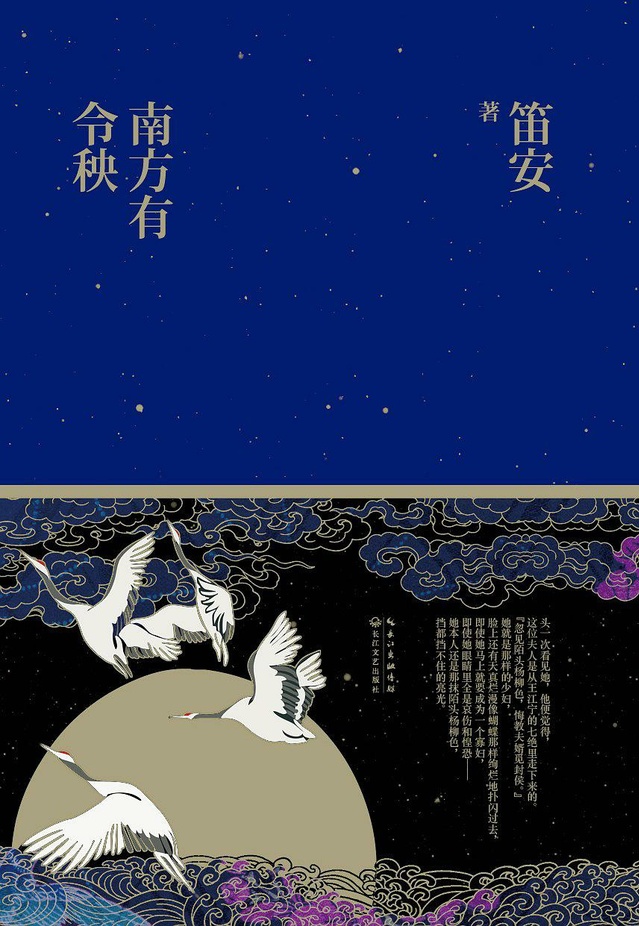
从秦朝的第一座贞节牌坊----女怀清台以来,贞节牌坊随朝代更替而起落,汉唐民风开放,贞节牌坊甚少修筑,宋明受理学影响,一座座贞节牌坊又拔地而起。千百年过去,人们只能通过牌坊的飞檐青瓦和牢固高耸来想象当年属于一个女人的至高荣耀,那些被动或主动、守寡或殉葬的女人,她们在那些时代有个名字,叫节妇。理学中有三纲,对于旧时女子来说,‘‘夫为妻纲’’已断了她们生命中的光,鲁迅先生把节妇称作鬼妻,也不无道理。漫漫长路只剩夜色,我们可以知晓节妇的压抑与痛苦,贞节牌坊代表的不仅是荣誉,也是黯淡的时光和灰白的生命,但不可知的是,她们中的一些人,在贫瘠的土地上奋力开放,爱与罚的因果循回,成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宿命。令秧这个江南女子,迈着她的三寸金莲,被大红花轿抬进了唐府,开始在黑夜惊鸿一舞,用生命等待爱火重燃,然后用生命去祭奠属于她的那一座-----贞节牌坊。
令秧嫁入唐家时才十六岁,次年丈夫唐简去世,令秧彼时还是个天真的孩子,她也想不到守寡意味着什么,只是单纯好奇着“死亡”这件事,所以会问唐简:老爷可以不死吗?好在唐简是个温厚的男人,令秧虽未在他身上收获到发自心底的爱,可他给了令秧最初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后来令秧在煎熬中回忆唐简坐在木椅上的沉稳样子,常常以为他还在。作者笛安也说,这本书写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成全。就像《霸王别姬》中程蝶衣说:做人得自己成全自己。我一直在想,如果唐简没有这么早去世,令秧的余生该如何度过,也许那会是另一个故事,但唯一不变的是,这个丈夫,这座宅院,这个时代,都是令秧不得不背负的枷锁,摆脱的唯一办法是死亡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贞节牌坊立起之日,令秧带着她与唐家九叔唐璞的孩子服毒自尽。她厌倦了在这枷锁之下苟且偷生的日子,她的爱情和自由是不被允许的,就让那座贞节牌坊代替她恪守贞洁,她要脱离繁重的肉体去追寻她要的自由,令秧为得到贞节牌坊做的那些事,可笑也可悲,看到她请求谢先生给自己女儿爱的自由时,对她再无丝毫怨意。她也曾有春水桃花般的十六岁,唐璞给了她生命中最后也最动人的一段爱情,览字至此,独怆然而泪下,庆幸她终于有了一段两情相悦、得之忘死的爱,那座贞节牌坊看似是对她熬了十五年守寡时日的标榜,不如说是她对这残忍世间最无情的嘲讽。
唐简去世后,令秧被唐家族人逼迫殉葬,所有的世俗权威和妇道规则硬生生压着令秧用活生生的命去祭奠。那晚她被关在黑屋子里,门婆子起了恻隐之心,哄骗众人诊出了令秧的喜脉,唐璞微微地攥住了拳头,也许她用不着去死了——他胸口划过一阵说不清的疼和宽慰,是什么时候把令秧放在心上呢,或许是他扶令秧起身时令秧柔声一句“多谢九叔”,爱是人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就像令秧一句话可以拨动唐璞的落寞和爱火。唐璞总是不知道怎么称呼她,“离在祠堂里见着你,已经十五年了”“我是特意叫他们演给你看的”。令秧长在他心里十五年了。人们很难对过去释怀,直到他们尝试之后彻底接受结果。唐璞在唐家族长六公去世时终于借《绣玉阁》提问,向令秧表白心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哪怕令秧得到了贞节牌坊后选择自由而结束生命,唐璞都是她终生躲不过的劫,可是劫也是缘,她甘愿为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沉沦。
谢舜珲这个遗世独立的失意读书人,无数次充当了为令秧争取贞节牌坊的军师。自己坐拥偌大的家业,落第后便全心投入风雅,自恃清高流连花丛的潇洒模样与宝玉很是相似。其实读完《南方有令秧》后,总是会纠结一个问题:谢舜珲对令秧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爱?归根到底,他与令秧其实是同一种人,在污浊世间追寻着自己的心,看到令秧在龌龊目光下仍坚持爱与自由,他很难不起同病相怜之意。他为令秧出谋划策,为令秧写戏让令秧的守节广为人知,哪怕令秧喝下毒酒前他也未拼死劝阻,只是答应令秧会让她的女儿大胆追爱,只有懂令秧,才会理解赞同她所做的事。“谢某只告诉夫人怎么做,人生在世本来就是受苦,若有人真能如夫人所说,全是真的,真到什么都不必去办,那便也不是人了,夫人说是不是呢?”他与令秧相互尊重,一起反抗时代的污浊,他和令秧,都不想成为人类里面的“一类人”,而想做“一个人”。故事将走到尽头,他用一杯好酒为令秧送行,然后回去,回去泯然众人。谢舜珲可以说是令秧的蓝颜知己,十五年的陪伴足以让两个内心孤独的人收获最纯粹的友情,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年代,男女大防恐避之不及,纯粹的情感尤显珍贵,而越珍贵越让人神往。唐府中的三小姐和少奶奶在情感与肉体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了同性之情,这爱在深府大院中显得纯粹与脆弱,大时代背景下的芸芸众生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可偏偏又有强者临驾于弱者之上,于是强者的言行举止成了核定弱者命运的至高标准。男人之间的感情可以是诗文唱和,可以是官场应酬,可以是礼尚往来,而两个身处深闺的弱女子之间产生的爱,最初迸发的悸动多是孤独,孤独的来源是她们早早注定的命运。
其实无论什么时代,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感到无奈,哪怕是如今的我们,又有几个能收获十全十美的爱,更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我们越得不到,就越向往。问题在于,我们一路向往,一路争取,一路反抗,到最后得到了些什么。我赞同心里有对爱与自由的渴望,更欣赏为爱与自由付出实际行动,可大多数事偏偏徒劳无功,结果不尽人意,我们只能从这不断奋战的过程中获取满足和平静。令秧是个特定背景下的虚拟人物,可她也藏在我们心里,孤独与抱团取暖,压抑与强势反抗,都是我们要经历的种种困难。令秧在唐府与云巧、蕙姨娘结下了患难友谊,没有女人间的嫉妒,只有相互心疼与扶持,一个原本独自行走在夜中央的人,突然有人愿意为她掌灯,与她同行,雪中送碳的温暖在任何时代都不容忽视。
小说结尾以一句他永远怀念她结束,他是谢舜晖,她是令秧,谢先生平安健康活到了八十一岁,也怀念令秧到了八十一岁。唐璞给了令秧最绚丽的爱火,文中却未提及令秧死后唐璞的态度,这爱到底说不出口。生为爱和名节,死为爱和自由,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我只能想象,她会化作风和雨,在这人间自由去爱。
